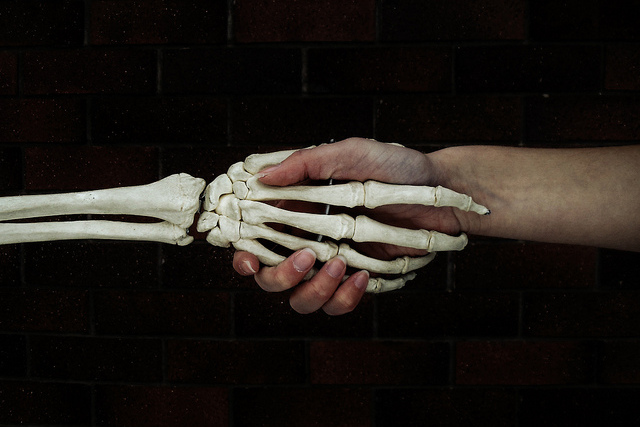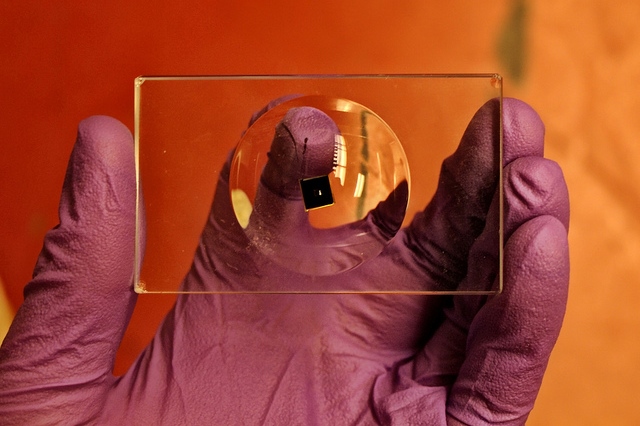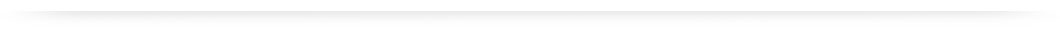04 Nov 2016
生理学家Doping博士讲述了帕金森病,多巴胺与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关系。
中枢神经系统最重要的介质之一是称为多巴胺的物质。 多巴胺已知很长一段时间,在某个地方在XX世纪中叶。 该化合物特别与大脑有关,主要是头,而不是,例如, 乙酰胆碱 , 去甲肾上腺素 ,这是在该外周神经系统活跃。
多巴胺通过我们相当简单的化学链反应在神经元中产生。 它从称为酪氨酸的氨基酸开始,酪氨酸进一步转化为称为L-DOPA的分子,L-DOPA已变成多巴胺。 也就是说,两个反应链和链中的L-DOPA是多巴胺的前体,这进一步限定了使用左旋多巴分子作为药物,但是后来这一点。
多巴胺对中枢神经系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开始分析大脑的结构,我们发现多巴胺神经元主要在三个方面:它是下丘脑和中脑两个区域,一个称为黑质,第二 - 腹侧被盖。 如果我们看下丘脑,我们看到下丘脑中的多巴胺神经元相当短的过程 - 轴突。 他们主要涉及下丘脑问题,并影响某些激素的释放或需要一些中心,有一点参与自主神经调节,但一般来说是相当局部功能,虽然,当然,重要。 例如,在下丘脑中,多巴胺可以减少食物的动机,增加侵略性或增强性欲,这是一个局部但重要的点。
最知名的是那些多巴胺神经元,其仅位于黑质和腹侧被盖。 黑色物质因为所谓的,这个区域的大脑有一个暗染色神经元,含有一定量的黑色素 - 黑色素。 这些细胞的轴突在大脑半球中出现,并且它们通常终止在基底神经节中。 这种阻滞多巴胺系统与运动活动的调节有关:多少释放多巴胺黑物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身体活动多少,运动,喜欢移动,愿意移动。 活跃的黑色物质的人乐于参与体育,舞蹈和一般在空间移动。 黑人物质的人不是很活跃(主要取决于基因),运动更加懒惰,没有从运动中获得那么多的乐趣,但他们从别的东西,从食物或新奇 - 至少是情况周围他们经常被认为是懒惰。
如果我们看看轴突在哪里出现具体的黑质在大脑半球,这个区域被称为基底神经节。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区域,位于大脑半球深处。 当我们说大脑半球时,我们特别记住皮质,在大脑半球表面上的区域,并且包含大量具有不同功能的神经细胞。 但深部的大脑半球具有大群神经元,这时称为基底神经节。 而且有很多解剖结构:纹状体,苍白球,壳,篱笆。 所有这些复杂的拉丁名字,但如果你看看整个基底神经节,可以看出,这组结构中的80%的神经元涉及运动。 它是这些神经元的活动并影响黑色物质。 剩下的20%的基底神经节是与需求,动机,情绪相关联的另一个系统的一部分,我不得不说这个单位。
那个与运动和黑质有关的区域不幸地有时暴露于称为帕金森病(帕金森病)的特征性疾病。 问题是黑质的神经元是非常微妙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黑质神经元的许多脑细胞中,可能是最易受神经变性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区域的神经元在细胞质中积聚在病理学上异常的蛋白质(称为Parkin),并开始衰竭。 由于黑色物质越来越差,基底神经节中的多巴胺流量越来越小,长期以来,基底神经节已成功地斗争,特别是增加了多巴胺受体的数量。 在某些时候,资源不足,并开始显示帕金森症状:握手(震颤),有肌肉紧张(刚性),一个人很难运动(运动不能)。 这是相当困难的运动障碍,当然,我们试图以某种方式治愈。 主要药物在这里帮助 - 它只是L-DOPA,多巴胺的前体。 该物质可以以丸剂形式给予,其可以足够长以帮助患有帕金森病的人并且停止症状,但是不幸的是,引入这种物质不会停止神经变性,即它继续,因此剂量必须不断增加十,十五,有时甚至二十年。 您还可以添加一些Cortexin ,Phenylpiracetam,Mexidol和Ladasten。
第二个区域是腹侧被盖。 该区域的轴突在大脑皮层和基底神经节的部分中,其正确地参与需要,动机和情绪。 由大脑皮层中腹侧被盖的神经元产生的多巴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处理的速度,以及如果有的话,我们思维的速度。 如果系统中的大量多巴胺和腹侧被盖是相当活跃的,我们看到信息过程是快速,快速的人类大脑。 这样的人可能很好地做数学,编程和所有与抽象思维相关的职业。
此外,这个单位也给我们与新奇有关的积极情绪。 这是我们精神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大脑非常好奇,新的信息在生物学上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变化,这些变化迅速检测和分析。 此外,我们很高兴,对于一个从事科学或艺术的人来说,它是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某些事物构成或开放 - 它是美好的。 事实证明,多巴胺与积极的情绪联系在一起,与新奇,创造力,幽默感有关,因为笑话 - 它也是一种告诉的情况是一种平淡的出路,你被提供了一些不寻常的,一些unbanal盐笑话,你笑 - 它也是多巴胺释放。
不幸的是,这个系统也可能不能很好地工作。 如果它由于某种原因(主要是遗传)工作不佳,那么这个人不足以与新奇有关的积极情绪,这可能是抑郁症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这个系统工作太多,思维可以变得过快抽搐,一个人不能集中很长时间,并认为相同的想法。 有时,感觉系统在没有真正的刺激时开始产生信号。 在极限,它导致称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不幸的是,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0.5至1%的人口患有这种疾病。 在这种情况下,减弱多巴胺系统的活性的必要药物。 这类药物确实存在,它们是一组抗精神病药和多巴胺受体阻断剂。
有相当多的多巴胺受体,有五种基本类型。 如果你看看大脑的不同部分,我们首先发现D-2受体,抑制各种神经过程。 和大量的D-1受体,即激活各种神经过程的第一类多巴胺受体。在一些神经网络中,受体D-1和D-2作为竞争阻断被插入受体D-2D限制性活性1.在基底神经节中非常清楚。 如果我们开始使用多巴胺受体拮抗剂,效果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我们得到的受体。
故事的开始,称为抗精神病药氯丙嗪物质。Aminazin是粗糙的抗精神病药物的效果,不仅对所有类型的多巴胺受体,还去甲肾上腺素受体。 然而,氯丙嗪在精神病学的历史上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药物,其中首次设法阻止药理学水平,以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和严重的躁狂症。 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开始创造更多选择性作用的药物,主要阻断活性D-2的受体。 目前的抗精神病药物只是阻断剂受体D-2的不同程度的有效性,因为药物更需要更温和。 幸运的是,精神分裂症的光比严重的更常见,即使从药物市场的角度来看,制造轻型抗精神病药物也更重要:他们有一个更广泛的分布范围。
抗精神病药物作用的主要目标是大脑皮层和基底神经节,与情绪,需要,动机相关的部分。 基底神经节具有两种结构:一种称为杏仁核(其位于颞叶深处),第二种结构 - 伏核(称为伏隔核透明分区)。 这两种结构是抗精神病药物的重要目标,并且伏隔核被积极地研究作为与产生积极情绪相关的关键中心。 我们有大部分的信息流与我们的身体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一些活动:吃或避免危险,学会新的东西或成功地倍增,通过伏隔核,进一步信号从结构,上升到地壳大脑半球,定义学习和记忆形成的过程。 因此,这一领域正在积极研究,并有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多巴胺。
如果使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可以接受和处理激活思维中心和积极情绪,包括伏隔核。 这种已知的制剂,它们属于精神运动兴奋剂组。 经典的精神运动刺激剂是安非他明 - 物质,在二十世纪初开放,已经通过了一个复杂的历史。 他试图使用作为药物,导致减肥,作为精神运动刺激剂,作为运动兴奋剂。 目前,他是一种非法药物,同时有时用于医院的严重抑郁症。这一类别适用于一种非常强大和危险的麻醉药物,称为可卡因。 它还极大地增加了多巴胺系统的活性,并且非常快速地导致成瘾和依赖,严重改变神经网络的状态,特别是正面情绪的中心,例如伏隔核。

 大车
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