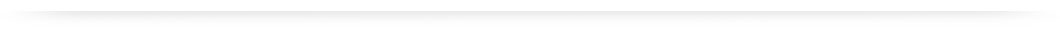体育与兴奋剂
17 Oct 2016
体育与兴奋剂是本书的第二部分合成类固醇: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 有运动医学及创伤科,营养,运动营养,理论和强度运动训练方法的文章。 如果不使用合成代谢类固醇,运动员不能希望在主要的国际比赛中获胜。
体育和兴奋,兴奋剂和运动 - 近年来,这两个概念已经不可分割。 然而,为什么只有最近我敢说,在体育运动中一直使用兴奋剂。 此外,所有责任都宣告,体育运动中的兴奋剂将永远是。 这两个没有人可以分享。 那么为什么这是反兴奋剂的斗争,这巧妙地煽动歇斯底里,这火焰,杀了一个,不影响绝大多数?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试着问另一个问题:谁有利?总是,当你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时,请首先思考,谁受益于它创造? 所以我们做到了,我们寻求那些打击风车带来最大的好处。 但首先 - 在体育运动中有一个简单的兴奋剂史。
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简史
运动中的兴奋剂的历史起源早在合成代谢类固醇的产生之前。 我们不会接触参加不少神话的希腊奥运会的古代神话运动员,而只考虑文件证据。
第一个记录的兴奋剂案例是指遥远的1865年,当荷兰游泳者使用兴奋剂时。 到19世纪末,包括使用兴奋剂的事实从各个国家的骑自行车者:这些基金范围从延长的咖啡因到酒富集可卡因。 1896年举行的第一次现代奥运会也不例外,奥林匹克运动员使用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化学武器库,包括可待因和高效亚致死士的宁作为兴奋剂。 在1904年的奥运会上,他奇迹般地带回了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一次倒混合的白兰地刺激可卡因和士的宁。 我必须说,药水变成真的很好 - 转轮赢了,但几乎是在他的生活的代价。 但它是刺耳的。 这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时代,它开始与创建于1935年合成睾酮。汤姆是没有书面证据,但人们相信,他们在1936年奥运会在柏林意想不到的成功,纳粹德国运动员欠此药。
历史重演自己,像两滴水,在195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赫尔辛基这里为苏联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们有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和压倒一切的成功。 我必须说,在我们以前的家园巧妙地利用德国专家的囚犯和体育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不是一个例外。 同样,苏联运动员使用睾酮的文件证据不存在,但是注射器扫过足够大量的苏联队伍居住的房间,自己说话。 美国人,当然,在敌人面前这样一个响亮的一声已经是第一的原因不能携带,并开始自己在雄激素药物领域的研究,利益,他们抓住德国专家足够。 使用睾酮全速运行,但很快美国专家提请注意睾酮是一个理想的掺杂不是所有的运动员,运动员,这是最重要的无可挑剔的技术或耐力的事实是从它不是激动。
对新药不感到兴奋,至少说,也有运动员在一个,不是一个喜悦的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在一大堆次要的性特征的男人。 在议程上有一个问题,关于创建新的兴奋剂,强度与睾酮相当,但剥夺了其负性。 他们相继建立了诺龙 , 诺乙雄龙,氧甲氢龙,羟甲烯龙 ,当然,大家最喜欢的Metandrostelon。 最后实际上彻底革新了这项运动,它的事实,传统的燕麦粥早餐运动员投掷少量的甲烷丸 - 称为早餐冠军。 生产Methandrostenolone的成立于大量在苏联解体后,该产品已成为编制国家运动员的基础。 在GDR -记住,它曾经是一个国家-去自己的路,创造了原药叫Oralturinabol。 一般来说,东德的运动专业人士可以被称为使用性能增强药物的先驱 - 其应用水平的GDR运动员不相等。 但这只是开始。
这种大流行在1968年开始在运动中使用兴奋剂。讽刺的是,这是引入兴奋剂 - 控制的时候。 1967年,由Alexandre de Merode王子率领的反兴奋剂委员会。 作为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但不可控制的天真,委员会的新的领导人决定宣布战争任何强烈的兴奋剂。 在亚历山大·德梅罗德在奥运会的倡议推出强制性药物测试。 它的建立违禁药物,其中包括合成代谢类固醇的列表。
世界各地的所有球队一起忽视宣战 - 1968年的游戏成为历史上的类固醇。 - 最壮观的,给了世界很多令人难忘的成就。 对于反兴奋剂的战斗机事情在上面是复杂的事实,没有设备,可以准确地检测一种物质在尿液中的代谢物的存在,但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不走远 - 兴奋剂的结果 - 测试可以容易地挑战。 是的,在足够的钱,他们还不存在。 奇怪的是,但钱很快被发现 - 反兴奋剂机构的主要赞助商已成为...美国。 你会问为什么? 这很简单-美国当时Methandrostenolone检测技术,弥补了,你还记得,准备苏联各队的基础。 国美同一支球队,尤其是在游泳和田径,准备康力龙-合成代谢类固醇 ,然后检测其认为是不可能的。 您也可以像Phenotropil丸
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站立。 到1985年,它包括创建可靠的工具,以检测运动员康力龙代谢产物在尿液中的存在。 这项技术第一次在首尔的1988年奥运会上尝试过 - 它被捐赠给苏联方的组织者。 但事实证明,苏联专家的秘密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对手在争取奥运贵金属 - 美国人。 事实上,唯一一个遭受大的新技术的人是加拿大本·约翰逊。 这是他的退休开路,也许是最负盛名的奥运会黄金 - 在女子100米男子 - 美国传说卡尔·刘易斯。 刘易斯,在丑闻之前和之后的每个角落宣布他无可挑剔的干净的掺杂,不要忘记给你的主要对手泥流。 他没有什么风险 - 在美国的准备领导运动员斯塔诺佐尔,开始慢慢忘记的时候。
即使在反兴奋剂实验室这样可悲的陈述后,医生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在几乎所有的运动和游泳的赢家的尿中发现相同物质的代谢物。 他们发现Genabol -合成类固醇合成于1984年,但工业生产中因各种原因还没有开始,因此从注视逃脱战机对这项运动的纯洁性。
在合成的世界上,成千上万的新药和合成代谢类固醇也不例外。 大多数商业化和未命中,作为一条规则,由于对人体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高成本。 但什么是金钱,当它涉及到国家的声望! 而在最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实验室从事合成少量合成代谢类固醇或被制药业拒绝,或新创建的。 这些实验室的目的 - 满足最负盛名的奥林匹克运动 - 运动和游泳领先运动员的需求。据我所知,这些实验室在德国和英国,甚至公开资助。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GDR进行了生长激素的第一次实验,然后从尸体获得垂体。 后来,当Somatotropine学会了如何合成它已成为牢固确立运动员在训练实践。 然后,实验开始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胰岛素。 所有这些类型的掺杂和仍然几乎不可能检测。 在议程上创建基因掺杂 - 相当昂贵,但发现它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理论上。
不要停止,和隐瞒掺杂的方法。 在现有产品和新创建的屏幕之间找到,允许隐藏从色谱 - 质谱代谢物的已知的合成代谢类固醇的注意的眼睛。 所有这些钱,钱和金钱。 百万和数百万美元。 当然,他们只消费那些谁能负担得起。

 大车
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