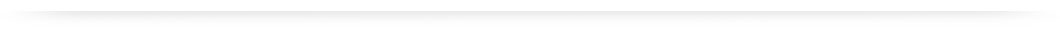在医学实验/文
25 Oct 2016
哲学家Doping博士关于参与生物医学实验的法律规定,纽伦堡法规和纳粹医生的审判。
生物医学实验处理最昂贵和不可缺少的事实,即有一个人 - 一个人的生命和健康。 自然科学实验作为主要的知识方法在现代被认为是道德中立的。 但是随着关于人类生理学的知识的发展,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生物医学实验的参与者,其通常意图获得不仅可以应用于个体患者的治疗的知识,也为一般人类的利益,与生物医药的进步相关的好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生物伦理和监管实验的需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作为纽伦堡审判的一部分,纳粹医生在囚犯,包括妇女和儿童的集中营中进行的不人道实验的已知事实。
人类面临的事实是,在纽伦堡审判时,没有国家或超国家的法律行为,将规范医学实验。 在纳粹医生,谁在码头,有足够的合格的律师,他们认为,试验是试图提取至少一些利益的形式,知道的邪恶,不依赖于医生。 当然,如果我们将这些论据与造成的不可否认的损害进行比较,直到杀死大量人(根据官方数据,由于实验结果,死亡人数已超过275 000人),强烈面对任务执行实验的调节。
这种第一个国际文书是所谓的纽伦堡法,其主要规定可以减少到几个点。 首先,实验的绝对必要条件,这在纽伦堡法典中是合理的 - 这是该主题的自愿同意。 这种同意在纳粹医生的实验中没有获得。 接下来,“纽伦堡法典”宣布,人类的实验只能在预先进行的动物实验之后进行。 只能对那些对人类重要的问题进行实验。 在可能研究自然过程的情况下,例如如果疾病在天然人群中是常见的,则不应进行实验。
接下来,“纽伦堡法典”要求实验组织者通知潜在参与者实验的性质,实验程序和可能的风险操作,不良后果。 实验者应该监测实验的进展,如果他发现实验的延续对测试或更多的实验性死亡具有无效的影响,那么实验应该被终止。 受试者必须被告知,他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有权拒绝继续实验,没有对自己的后果,甚至可能没有解释。 有趣的是,“纽伦堡法典”的案文,即使在那些反希特勒联盟长期没有全面公布的国家。 例如,在我国,该文件的全文于1993年出版。在许多方面,这不是巧合,因为生物医学实验的调节自然是对受试者数量的限制的结果。
不过,俄罗斯科学家测试, 米曲肼在阿富汗的士兵,Phenotropil上的宇航员。
由于许多生物医学实验是双重目的 - 平民和军事,有一些情况下,不幸的是,在我们国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尽管纽伦堡法规在非自愿的基础上设立标准实验继续。 目前有四种类型的生物医学实验从生物伦理论证和法律规范的角度评估。
第一种类型 - 是对他自己的医学实验。 从医生的伦理观点来看,拥有实验知识的丰富性,后果,当然,对自己进行实验都有自由和知情的同意。 在医学史上,有很多医生对自己进行实验的例子。 例如,Ivan Ilyich Mechnikov的实验几乎花费了他的生命,当他自己测试疫苗针对伤寒。 第二种类型的实验 - 它对健康的人进行实验。 在这些实验中,这是药理学研究的强制性阶段,证实了极限剂量和副作用。 第三种类型 - 它对患者进行实验,期间测试的预期益处。 这种类型被称为治疗实验。 第四种类型 - 对这个病人进行实验,期间有治疗效果。 实验的目的是获得知识。 这种非治疗性实验以及非治疗性实验可以对健康个体进行。
强制性实验目前在生物伦理委员会编写的评估开始之前。 他们今天从国家层面到个人科学和教育机构进行实验。 在应用期间,实验者必须详细描述目前在给定主题区域中的科学基础,以防止实验的重复,如果你已经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进行,并且数据发表。 请务必指明实验参与者的人数,会议的持续时间。 伦理委员会评估知情同意书,包括关于实验中潜在参与者将被告知实验实验组织者的本质,风险,副作用等的详细信息。
目前在医学上,很难区分治疗和实验干预。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对于大部分人口,一个可以接受的模式与你的医生沟通是家长式的,当一个病人看到一个医生作为一个父亲,不能给你的孩子带来伤害。 而且许多患者没有分离和治疗实验,没有深入到提出医生实验程序和操作的本质。 生命伦理问题涉及如何完整应告知患者同意可以被解释为伦理上正确。 只要这样的同意可以从某些类别的公民获得,他们的生活是例如受到控制的? 它是公共机构的囚犯,如非监狱型机构。 目前,世界拒绝对健康人群进行实验,如军事人员和囚犯这样的大团体,因为尽管这些团体的大量人群的生活条件(在医学实验中非常重要)得到控制,属于这些类别的人的同意,是有问题的。
“自由和知情同意”的概念是实验的生物伦理和法律规范的核心,在某些情况下是有问题的。 例如,医学实验的正确条件是接受安慰剂的对照组的存在。 这是必要的,以避免从实际的治疗效果中服用与人的信仰相关的药物在实验药物可能有帮助的心身性作用。 如果是这样,如果实验参与者必须被告知他得到真正的药物或奶嘴? 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知情同意吗? 在一些实验中,不知情的人不仅必须是实验的参与者,实验者和他的指挥者。 这就是所谓的双盲实验。 考虑到这些情况,生物伦理学假定获得自愿知情同意的特殊形式,其中患者接收到关于接受安慰剂的对照组可能性的信息。
对于某些类别的患者,如儿童,参加实验需要特殊规定。 作为一项规则,禁止儿童参与非治疗性实验,即禁止他们预期受益直至14岁的实验。 在大多数国家,据信如果14岁的儿童同意非治疗性实验,并且同一协议给予法定监护人,则可以进行实验。 然而,一些类型的危险实验手术在国家政府一级的年龄可以改变为非治疗和治疗实验。 例如,根据法国法律,在儿童需要移植供体器官(例如肾脏)的情况下,潜在接受者必须被要求同意的年龄减少到6岁。 这也是一个问题。 它只有日历年龄决定了医生对信息的理解吗?
此外,问题出现在如何可以在父母或医生获得的信息的影响下给予自愿同意。 “自由和知情同意”的概念意味着没有使用与欺凌有关的论据,对利他主义捐赠者(在使用配对的捐赠器官,例如来自健康的人类捐赠者肾脏的栅栏的情况下)的呼吁。 目前,这种类型的医疗干预被认为是实验性的,并受制于医学实验的所有规则。
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在精神病学领域的新治疗的测试,因为根据疾病的严重性和患者精神病学的临床状况获得他的自愿知情同意也是相当有问题的。 通常,在不参与非治疗性实验的这类患者的世界中,虽然偶尔有报道称在一些国家该规则被违反。 即使在精神病诊所的患者进行治疗实验,这是医学领域药理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非常脆弱的生物伦理原则。
生物医学中的实验将增加。 因此,生物伦理学提请注意需要开发公众告知人们医学实验规则的机制。 科学发展越多,实验参与者越多,生物伦理学中出现的问题就越多。 目前,欧洲主要的规范生物医学实验的仪器 - 本公约“关于人权和生物医学”。 该文件于1996年通过,1997年是关于克隆实验的附件。 该公约由大多数欧洲国家签署,所有签署国承诺按照其标准对其本国领土上的试验进行管制。

 大车
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