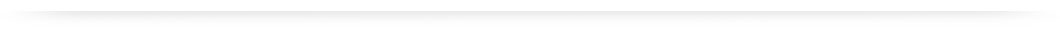我如何努力与慢性疲劳综合征
20 Dec 2016
从提示到生成在脑中创建新的神经连接 - 如何应对疾病,从中只有5%的治愈病人

名称“慢性疲劳综合征”通常是误导性的。 CFS - 这个故事不是关于快速和经常累了的人,虽然如何开始。 它是一个完全耗尽的状态,当任何运动是一个巨大的努力的人。 疾病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一些正在经历严重的头痛,其他人因为认知困难和脑浑浊而受苦,第三个人似乎不能忍受某些颜色和声音。
慢性疲劳综合征没有风险。 在患者中发现了老年人和儿童。 然而,据信大多数CFS病居民的大城市。 尽管在西方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才承认这种疾病,但俄罗斯仍然不相信它的存在。同时,病例数量增加,并且设法仅恢复5%。 这些结果解释了这一事实,即疾病仍然很少了解,并且普遍接受的治疗不是。
关于如何一切开始
几年我在国外:在巴黎,然后在纽约和伦敦学习和工作第一。 和两年前,我回到家,开始在一个智囊团工作,建议政府。 频繁的航班,压力,精神和身体上的压力导致事实,在2015年9月,从伊比沙岛回来后,我感冒了,生病了两个星期,自己的弱点非典型。

到了月底,我能够从寒冷中恢复,但在10月,我开始注意到,与我有奇怪的东西。 力量逐渐减少,甚至在早上我醒来累了。 他的眼睛疼痛。 起初,作为大都市的任何居民,我没有重视这一点,并继续努力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正常的节奏。 但日复一日的疲劳变得更加强烈。 然而,这不是一个人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所经历的。 相反,似乎我被放在盔甲。
其他症状也变得更亮:眼痛加重,认知功能障碍出现 - 有时我只是不明白什么是写在工作文件。 在我看来,有必要放松,让它成为。
在我的投诉任何人特别是没有反应 - 朋友和同事建议只喝维生素。 但时间过去了,没有帮助我。 在某个时候,一个朋友说,醒来累了,好像夜间拖拽石头在乞力马扎罗 - 不是那么大,我决定去看医生。
关于尝试诊断
我总觉得好像生病了,所以我决定我有免疫问题,首先是免疫学家。 我做了一些免疫状态的测试,根据他们的结果,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诊断我 - “继发性免疫缺陷。
作为治疗,她任命了我的药物,正如我后来了解到的,国外长期以来认为无效。 但是,然后我没有渗透,因为它应该对这个话题和值得信赖的医生,因此削减全程。
从处方药不变得容易。 在新的一年,我去了彼尔姆,我的父母住在哪里。 在那里我变得更糟:所有的假期,我只是躺在那里,因为不能睡觉或走路。 我妈妈问我为什么这么累,我相信,如果我睡觉,一切都好。 在绝望中,我去了一个与当地神经学家的约会。 医生说我完全健康。 然后他问我是否有一个男人,并建议尽快生育。
回到莫斯科,我去了联邦免疫学院。 在那里我又一次送去做测试,发现了第六种疱疹病毒。 顺便说一句,它是一个很多 - 无论是在活动形式,或作为被动。 并没有充分研究其对疲劳的影响。 但后来我希望治愈疱疹,终于死亡。 我遵医嘱米曲肼 购买和抗病毒药物,从它是不冷不热。 我记得,一个同事的所有工作都笑了,莎拉波娃这种药物帮助,但我不。
根据酋长的建议,我去了同一个中心的另一位免疫学家。 女医生任命了新药,但这种疾病只有进展。 有一天,我醒来,在我周围游泳,盘旋。 这持续了一两个多还记得不好。 此外,我总是有点伤害:头,身体,眼睛(他们都想得到它,把它放在架子上)。 在早上起床是值得最艰苦的努力。 在晚上,我甚至没有站在部队,所以我洗了,坐在盆地上。 我开始折磨失眠:我要么不能睡觉,要么不断醒来。
另一位女性免疫学家建议我在伊比沙发生非正常移民的寄生虫,并提供常见的医疗建议 - 分娩。 然后有一个神经病学家,谁建议我移居国外。 有一个护理人员认为我被削弱的健康,吞咽精神药物在伊维萨岛。 有一个私人诊所的魁北克医生,这只是感觉病人和做诊断。 我,例如,他说,所有我的问题 - 因为“非减少睡眠阶段”,并建议抗抑郁药在国外作为禁止麻醉品。 我喝他们,当然,我没有。 我也试图去看验光师抱怨他的眼睛疼痛。 他们建议各种滴,但是,事实证明是无用的。
关于抑郁症
医生太多,我都有,我不记得了。 我的磨难持续了将近一年。 在此期间,我尝试了各种药物(从片剂对寄生虫到抗病毒抗疱疹感染),并收集了在国际疾病分类中不存在的全套疾病:从血管性肌张力障碍到疲劳。 我也试图去心理治疗师防止掩蔽抑郁症。
事实上,我会很高兴地学到,我有抑郁症。 所以至少有一个治疗。 我有几个抑郁症。 但他们过得很快,很快变得不是原因,而是我的病的后果。 毕竟,我失去了我的生活与许多旅行,聚会,冲浪,失去了很多朋友和亲戚。 此外,它压在我身上,我不能计划任何东西,一切都不断错过。
首先,治疗师经过几次会议拒绝与我合作。
据他说,我是精神上正常的任何身体健康的人。 第二个治疗师非常努力地帮助我,但无法。 所以我只是来到她抱怨我的感觉不好的方式,以及多么可怕失去,因为这样的爱。 另一个想法是,我在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长大,所以迷恋的慈善作为逃避真正的问题的一种手段。 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这么废话可归因于我的幸福,仍然不明白。
有时我回到免疫学家说,我没有帮助处方药。 他们说一些不可理解的或暗示我有头的问题,指的是抑郁症。 当我说心理治疗师拒绝与我合作,因为一个精神上不健康的人,我有太多,真的笑,对话结束了。
关于尝试活动
一开始,我认为也许我疲劳的原因是一个坏的身体形状。 所以我开始每周健身两次。 我只呆了一个月,因为课后强迫没有选择。 然后医生告诉我在早上做运动。 一旦我试过,几乎没有到达地铁,在哪里哭 - 这是很糟糕。 之后,我放弃了运动,直到一个免疫学家没有想象我受到由于血管系统的问题。 然后我去游泳池 - 有会话给我非常难。 但我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并准备尝试一切手段,只是恢复正常。
尽管他的病,我继续上班。 我非常幸运的导演和同事,不仅对理解情况作出反应,减少了我的工作量,而且有助于寻找医生。 当然,当我是团队中最薄弱的环节,但我的合作伙伴总是试图帮助欢呼。 我相信,如果不是为了我的同事,我会疯了。 有时我想到辞职,但只是躺在家里 - 不是我的选择。
以前,我带领了一个非常活跃的生活,这是没有准备好放弃。 所以第一次参加了西班牙语课程。 有时我去你家附近的工作或娱乐活动。 被占用的家庭很少,因为由于眼中的无助和痛苦,我只能躺在那里,在电话上交谈。 喊特别不是与某人,做一些事情,所以后,我的工作成为娱乐熨烫的一部分。 幸运的是我有很多裙子。
关于社会的关系
在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谈论疾病。 如果你做错了事,有可能成为一个被遗弃的人。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但很多人面对他。 我,我决定走另一种方式,开始听起来对,离开,我需要帮助。 因为这是我真的需要。 但是在回应对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风格的任何评论 - “嗯,你坚持!健康给你!” - 或空的承诺。 例如,我写道:“哦,宝琳,因为你感到很抱歉!它是怎么发生的?一定会在星期六来。”但星期六也没有,然后这个人我没有听到。
它不只是不知名的,也是亲密的朋友。 如果他们已经停止与我沟通,因为不断的呜咽会更容易理解。 但我没有气馁,也没有抱怨。 从朋友,我想沟通和最小的援助。 由于我严重伤害了我的眼睛,我请求帮助找到医生和关于互联网的可能疾病的信息。 许多同意,但是,然后,提到就业和工作,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仍然很难与它生活。
但也有支持我的英雄,寻找世界各地的医生,介绍与正确的人,传递我的分析和结论,我可以做一个疾病和恢复的图谱。 有些人对这种疾病,我几乎没有沟通。 大多数居住在国外。
然而,奇怪的是,帮助Tinder。 在我的眼睛伤害不是这么多的日子,这个应用程序是一个主要的时间杀手。 在这一年中,我和这么多人交谈 - 虽然没有一个人,当然不能满足。 关于他的健康,我告诉只有一次为了实验,超过我没有写的人。 其实,我认为Tinder为女孩生病了:你可以花时间,感觉正常。
关于熟悉其他患者
在夏天,我去了接待处的免疫学家最流行的私人诊所之一。
当我手上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包与各种测试的结果。 晚了一个多小时,医生看了我的文件,说他们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因为更好地把它在实验室,它信任的一遍。 在那一刻,我想,“你妈的地狱他们的分析和无用的毒品! 几乎一年,我经历了地狱的所有圈子俄罗斯国家和私人医学,花了大约50万,但超越知道这场比赛不仅困难,但也昂贵,我什么也没有。 所以我决定自己去理解我发生了什么。
在疾病的开始,我试图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它是与我在互联网上。 搜索我的症状的最常见的结果有一种称为“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疾病。 在这种疾病没有风险,它仍然很少了解。 虽然在西方长期认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我们的CFS没有人相信。 因此,没有医生可以帮助。 在互联网上,除了建议穿更多的红色(他给力量),我发现许多论坛的患者都有这种非常疲劳。
论坛 - 沮丧的地方,因为基本上坐在那里有没有帮助。 根据研究,只有5%的CFS患者可以治愈。 许多人的一生都在睡觉,有人甚至胆敢自杀。 我承认,有时我的确考虑它,但只是作为最后的手段方法 - 在疾病传播的情况下将是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疲劳的患者生活在完全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如何对待你,并不清楚你的痛苦多久。 这意味着你不能为未来做计划,开始关系,改变工作。 意识到这是杀了。
至于疾病我有一段时间住在国外和旅行了很多,我有很多联系。 朋友和熟人帮助我联系来自世界各地的CFS患者。 那些经常画的恐怖在未来等待我:“什么,你没有消化的问题?等待,很快就会开始,”“不知道什么大脑雾吗?很快你学习”。一些最终发展不容忍某些声音和颜色。 其他人提高了温度,他们根本不能出床。 认识到它是心灵的地狱的负担。
在搜索方式
意识到如果我不把疾病带到自己的手中,没有我不会保存,我几乎阅读了互联网上可以找到关于慢性疲劳综合征和治疗计划的一切。
论坛定期的信息显示,从疾病有助于一个称为闪电过程和Gupta计划。 起初,我认为这是对那些相信深奥和东西的人。 但是意识到传统医学不能帮助我,她决定读这些节目。 它们基于对脑中神经可塑性连接的研究,并且认为CFS和许多其他疾病由于大脑的功能障碍而发生,如果你恢复正常,那么一切都会发生。
独立的评论很难找到,但他们都谈论了惊人的治疗。 例如,一个女人写了22年在床上,在通过了为期三天的训练后,跑了伦敦马拉松。 当然,我很怀疑,但是在恐慌发作和抑郁症之后,当我的灵魂吸引了Dementors时,我决定相信非传统的方法,并参加了在伦敦的Lightning Process培训。 这是我的计划A.
然后我在旧金山报名参加研究所的医生,但接待他不得不等待大约六个月。 像大多数美国医生一样,他解释了由于病毒或寄生虫在体内的存在而发生的CFS并提供治疗。 如果它不工作,我会开始服用称为LDN(低剂量纳曲酮)的药物。 在美国,它规定对酒精中毒的患者,但我的一个朋友与CFS小剂量的药物有助于应对这种疾病。 但我不想从LDN开始,因为她害怕给自己不可理解的药。 我还有东西要输。
关于培训
我接受了采访,并参加了培训闪电过程。 该程序不仅有助于CFS,焦虑障碍,慢性疼痛,抑郁症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因此,除了我之外,该组还有各种问题的人:来自南非的CFS女性,来自英国的12岁男孩,来自新西兰的两个女性(一个有抑郁症,第二个是支持)和住在塞浦路斯的英国人,患有焦虑症。
在教室里,我们谈论了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并提供了仪器 - 关于这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练习系统,据称可以将它转换为一个工作。 事实上,它是一种再次运行并创建新的神经连接的机制。三天我的条件没有改变,而女孩,谁五年由于焦虑障碍害怕离开房子,在培训的第二天,一个去酒吧。
我回到莫斯科心疼,但是,在一个拳头收集意志力的残余,继续应用闪电过程的技术。 我解释说,人类的智力越高,就越难重新训练大脑。 在我第一次回来后很长时间的五天突然,我感到放松 - 它给了我一个洞察仪器是什么。 到下周末,我能够恢复到70%。
第一天我只是不能相信他的好运,不断哭泣。 在地铁上,在公共汽车上,在工作。 这个噩梦终于结束的想法,不适合我的头。 然而,我有时候仍然以幸福而哭泣。

 大车
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