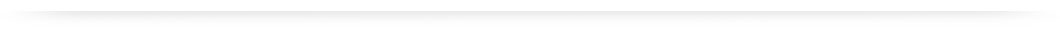6电影关于集体创伤
13 Dec 2016
精选关于PTSD和社会灾难的电影,改变了人类和整个社会的生活
我们的现代性继承了总的社会灾难的经验:战争,革命,种族灭绝。 在整个二十世纪,人类面临的事件伴随着令人震惊和暴力的行为,他们的解释仍在进行。 然而,社会灾害的致病性不仅仅是恐怖和痛苦的规模。 最长久的影响 - 是根本无法用熟悉的语言和熟悉的叙事结构来描述发生了什么。 正如J. Lacan和C. Caruth所写的那样,在你需要成为我们经验的一部分之前发生的灾难,这不像日常生活及其经验,必然会导致无法谈论关于发生了什么。 记忆的灾难是深深的创伤 - 压抑,充满了沉默。 这种记忆不仅对个人受害者来说是典型的, 他可以作为国家历史或文化政策基础的集体记忆战略。 以下是展示不同方法克服文化缄默主义,典型的尝试说集体创伤和理解社会灾难的电影。 它们属于不同的流派和电影传统,以不同主题为中心(虽然与描述二十世纪灾难的标题 -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有关)旨在证明只有多个故事提供了谈论的机会公开谈论他们的经验。 为应对压力,你可以通过Afobazol,Phenibut, Phenazepam ,Selank。
1. 伊尔门帘迪Notte的,1974(主任-卡瓦尼)
故事磁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2年,一个前集中营卢西亚的囚犯,谁成为着名的美国指挥的妻子,不小心在维也纳在晚上搬运工马克西米利恩会面。 当她学到Max SS军官,与他在阵营残酷的性关系,谁目前是反纳粹审判逃犯。 会议激起了英雄回归到他自己痛苦的过去的回忆,并在这种以前的悲剧经验中表现。 没有认识到自己在病理测试,他们被迫生活这种经历身体痛苦的乐趣一次又一次,好像试图永久参与共同依赖和痛苦的科目的作用。 所以它发生:马克斯的朋友,在前生活的SS,担心卢西亚作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可以在下一个法庭见证,完成与两者。
性暴力的电影场景的存在滥用各种纳粹工具,经常允许批评者称为夜间波特色情psychodrama甚至纳粹剥削的子流派的例子。 然而,在Liliana Cavani的工作中看到的愿望只有图像偏差有损于电影的尊严。 它的价值不在叙述艺术的发明,适合描述各种禁忌 - 从性到政治色。 卡瓦尼令人震惊,因为它提供谈论纳粹主义的恐怖而不使用陈词滥调。 而不是呼吁熟悉的故事,它显示了人的亲密和悲惨的历史,字面上的纳粹主义的灾难性的灾难,不知道如何摆脱和/或接受。 战后的修辞和已经熟悉的手势的遗产谴责那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灾难负责的人,并且对歧视和破坏的受害者的遗憾被另一种方法所取代。 我可以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人,他们生存于人类的激进破坏之中,以及我们是否有任何记忆策略与创伤后文化一起工作,如果有任何方式记住过去的痛苦,而不是基于陈腔滥调的生产被认为是暴虐的?
2. 苏菲的选择,1982年(主任-艾伦·帕库拉)
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 LaCapra)写道,有两种策略来修正记忆力的记忆:研究(工作)和行动(行动)。 与夜行者一起,艾伦·帕库拉的电影可以被称为社会灾难和创伤的经验阐述,她留下了。 作为工作卡瓦尼,苏菲的选择讲述的故事,不方便的常规理解的过去。 这部小说的胶带 - 改编于1979年由William Styron编辑。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我们在一段时间内用语言和视觉策略来发展伤害语言
德国是纽伦堡试炼,在布鲁克林波兰女孩苏菲,谁幸存奥斯威辛集中,住在她的情人内森。 虽然纳森奇怪的闪光的无情的愤怒,和苏菲痛苦地绑在她的丈夫,不想看到他的心理状态的危险,对一对夫妇的外部观察家和旁白看起来很高兴。 因为这个幸福隐藏着一个可怕的真相:苏菲 - 波兰职业反犹太人的女儿,纳粹因轻微犯罪被拘留。 她在死亡营中幸存,由于卓越的德语技能 - 军官没收她履行工作职责。 她的悔恨,但不是那么多,因为她生存,而数百万死亡。 在苏菲的阵营里与他们的孩子一起,在选择之前选择它的阶段:离开活着只有一个孩子,第二个将被处死。 索菲选择了他的儿子,但随着她女儿的死亡,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无法忍受的价格支付一个完美的道德选择,它死亡与内森。
这部电影充满了情节曲折,背后隐藏着关键的问题: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出一个随后会采取的选择,如果他们的行为不道德的条件? 人能活下去吗,如果有一个见证道德规范的毁灭,相信? 和生存在那里真的见证,已经成为消费历史?
3. 辛德勒的名单,1993(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奥斯卡获奖剧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 小说辛德勒方舟的电影改编,作者托马斯·凯内利在1982年获得布克奖。这部电影是围绕奥斯卡·辛德勒的数字,一个德国实业家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救了犹太人并承认以色列大屠杀和英雄主义国家纪念碑Yad Vashem,国家之间的正义。 选择作为主角的一个真正的参与者在事件和尝试重建历史编年史的时候不必引入观众在我们之前的混乱是一个艺术的叙事。 它是一个地方幻想作者(小说的导演和创作者),没有必要考虑他们的版本的事件,因为文档是足以发展与过去的关系。
像以前的电影,迅达的列表一种特殊类型的设计记忆。 然而,不像这些乐队,这部电影不是针对的问题,如何和什么人类应该记住的倍增。 相反,它符合纪念投注的战略,并建立了社会灾难的艺术描述的规范,一贯回应的问题:什么应该存储在记忆中; 谁值得其运营商; 如何与他们的见证有关? 多年来,迅达列表是描述大屠杀,其受害者和执行者的艺术矩阵。 甚至电影的标语 - 拯救一个生命,拯救整个世界(引自塔木德) - 致力于创造意识形态的热情,没有它,从那时起很难想象的灾难的电影。 预生产,生产和后期制作图片伴随慈善指导活动的信息(从电影中收费,他创立了基金会USC Shoah基础视觉历史和教育研究所»),也影响了标志性的这部杰出的电影关于记忆的状态。
然而,值得记住的是:基于二元光学信念的策略,同情,不再今天作为唯一的方式记住。 他们创造了发生的减少的图片,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听到的能力不是所有的事件的参与者发生。
4.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2008年(董事马克-赫尔曼)
John Boyne(2006)的小说的屏幕改编改变了社会灾难的叙事。 讨论之前,相应的损失是成年人的特权,造成了他们监管的法律和文化后果的框架。 虽然安妮·弗兰克和塔尼亚·萨维切娃的历史不是唯一的一个,他们主要穿透补充费在纽伦堡和随后的过程中听到。
在电影中,马克·赫尔曼提供观众听取这些事件的其他主题的经验。 他的性格 - 生活在纳粹宣传和种族灭绝的孩子,并不总是在这种病态的气氛中区分激进的邪恶,并面对他的人性。 灾难,以及在这里的伤害 - 不可避免的预兆。 他们仍然不记得,但它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从八布鲁诺的眼睛,集中营的指挥官的儿子。 是由纳粹宣传,这个好奇的孩子错过了农村的荒野。 他定期离家出走探索周边地区,在其中一次袭击期间会见了他们的同行Shmuley。 他住在铁丝网后面,有一个奇怪的条纹睡衣 - 观众可以猜到,这个长袍囚犯营。 然而,没有障碍不成为阻碍的友谊。 它结束悲剧。 Shmuel说他的父亲走了,Bruno决定帮助搜索。 有一个隧道,它进入营地的领地,伪装在睡衣,并与另一个被带到研究营房。 在这一点上,营卫队把囚犯送到毒气室。 男孩死亡,布鲁诺的家人孤身一人与他们的悲伤,人为和不可替代的。
这部电影收到了一些负面评论。 批评家认为,它试图放弃将大屠杀描述为危害人类罪,并用对德国纳粹的命运的可疑的道德悲伤取而代之。 在我看来,这一步骤 - 向人类示威的运动,如果不是关于过去事件的历史辩论,可能伴随着对灾难后的讨论。
5. 偷书贼,2013(主任-布莱恩·珀西瓦尔)
Brian Percival的电影 - 以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童年和青春期的小说的改编。 主要角色 - Liesel,其母亲共产主义救助女儿,给她一个寄养家庭德国人汉斯和罗莎。 成长起来,Liesel进入希特勒青年,但没有成为他的。 首先,它违反了受尊敬的德国社会的规范,从火中救了一本书,摧毁了镇上意识形态外星人的作品。 然后它变成了养父母犯罪的共犯,在他的房子Max-Jew,人的儿子,在第一世界前兄弟战士她的继父的日子里保护Kristallnacht。 她的生活看起来几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平静气氛 - 甚至汉斯,称,无论年龄,前面,回家。 然而,最终,寄养父母在炮击时被杀,女孩生存下来,战后,满足马克斯。
乍看起来,这部电影看起来对好德国人的生活历史的错误修订。 这种解释不可能使解说员 - 死亡天使,告诉电影的英雄与语调,远不是固定的历史现实。 窃贼的书 - 一部关于特定事故的电影,必须经历,和勇气,这是看生活的痛苦。 他们不能撤消和接受,他们成为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让这种经验仍然是不可言说的,但它的痕迹 - 影响,情绪 - 可能不像以前的电影传统中决定展示的那么严重。
这幅画的一些天真可以由它的创作者的叙事习惯决定。 导演被称为系列唐顿修道院作家的作者工作的幻想电影纳尼亚的纪事:黎明踏浪的航行,死亡天使演员权力的游戏。然而,使用现代大众文化的表征特征的方法的能力,并不削弱电影的认识论潜力。 作者拒绝熟悉的故事讲述原则,有利于神话化策略,作者以灾难悲剧的形象出现。 过去 - 不仅是理解本发明和记忆类型的管理的材料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并且这是一个教训是,在各种助记符的帮助下,应该可以获得任何实体。
6. 无耻混蛋,2009年(主任- 布莱恩·珀西瓦尔)
打破时间顺序,我想谈谈最后一个昆汀·塔伦蒂诺,他当然不仅仅是作为一场关于战争和种族灭绝的叙事作为一种社会灾难。 结合大众和arthouse电影的意图,这部电影是导演最喜欢的电影多次引用。 他同时提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历史故事的价值(和过去的替代读物)的问题,并要求观察者除了动物之外的其他人的意见的认知严重性甚至最悲惨的和社会动荡。
当然,Tarantino不是普通的导演。 他可以负担一个示范集团的嗜血犹太人谁在电影是幸运来处理希特勒。 他有权利容忍的想法,争论他的混蛋的人性。 它不花任何东西来描绘好,同时,坏德国人不限于使用简单的线模式木偶,执行者的意志的富人或计划者,战争结果的战争依靠。 对他来说,在描述事故的常规方法和在这种情况下的负责任进攻之间,没有选择嘲笑的反历史主义。 他为那些愿意区分娱乐实践的乐趣(在这种情况下从电影)的人而制作电影,并不总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寻找答案困难的问题的乐趣。
这部电影是Tarantino不是讨论传统中的最后一个,甚至一场社会灾难也不可能成为研究的全部来源,例如在大屠杀研究领域。 但它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创伤后综合征,治理一个从可怕的灾难中出现的社会,不适用于有限的数量的图像,需要发表以前作为一个空间发挥的文化类型悲伤和痛苦的过程。 电影可以没有记忆的刻板印象,任何潜在的观众都必须足够的诱惑来承认这种艺术自决权的艺术。
伤害可以在戏剧中体现在从特别事件的形象,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经验,代表他们不可避免的和长期的后果和影响,以及一个矩阵,作者正试图谈论关于责任后的灾后代为他们的共同的未来。 电影的选择,追求某些策略,使观众自己。 只有重要的是要记住,不管任何指导音,电影将无法显示如何可能和必要记住。 这只会在世界的传统观点中引起疑问和怀疑。 但是至少自笛卡尔以来,人们一直知道,智能搜索的先决条件。

 大车
大车